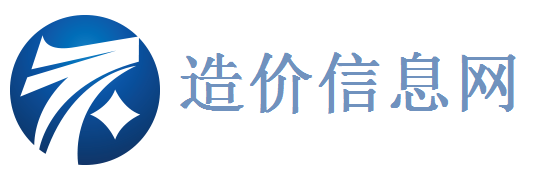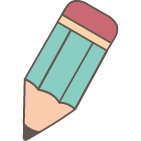关于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这样理解正确吗?
“国以民为本,民以土为生”,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生存保障与财富来源,土地制度深刻影响着民生状况,民生状况切实推动了土地制度的演化。
古代土地所有制主要有皇权支配或私有下的名义国有制、地主私有制与农民私有制三种形式,随王朝统治者、地主、农民等主体力量与地位的变化而经常调整且蕴含着民生演化之逻辑。
关于汉朝土地制度,已有诸多讨论,但通常局限于土地制度本身,如土地制度类型、地权转换与运动方式、中西土地制度比较以及汉朝具体阶段的土地制度特征等。
诚然,也有研究关注与土地密切联系的相关制度,如汉朝赋税政策、人口政策等,但较少从民生发展演化的视角探究汉朝土地制度变迁过程及其逻辑。
通过梳理汉朝土地制度变迁过程,分析其与民生状况的互动演化关系,以期厘析二者联动的内在机理与逻辑进路,从而助益认清土地与民生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
汉朝思想家吸取秦朝灭亡教训,重扬“民本”思想,关注民众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以“无为而治”为代表的“黄老之学”,耦合了汉初历经战乱、民生凋敝亟须“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
比如《淮南子》强调重民安民:“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除道家思想之外,儒学思想家以仁政论作为民生思想的理论基础,强调民为“立国之本”,国家稳定和政权巩固必须“得民心”,且关键在于“行以仁义为本”。
作为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贾谊总结秦朝灭亡之教训,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认为治国必须顺应民意以得民心,不得轻视更不可欺侮愚弄民众。
汉代思想家通过汲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并与彼时社会现实相结合,将“安顿民生”视为治国安邦之要务,认为应顺民意安民心,与民休息,尊天道保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先秦“民本”思想。
汉朝民生思想认为君主应体察民生,减轻徭役,德主刑辅,抑强扶弱,以安定社会整体秩序。《淮南子》提出“仁君明主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劝诫君主应节制欲望,轻赋少税,少征力役,减轻民众生活负担。
传承董仲舒的“德治”观点,东汉王符主张“恤民”“效功百姓”,劝诫君主“藉田有制”,反对贵戚“多受茅土”,确保民众拥有足够的土地。
荀悦认为当政者应做到“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并以“汤祷桑林,邾迁于绎,景祠于旱”为例进一步论证何谓爱民。
在土地制度方面,他主张“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民弱,以防兼并”,以此抑制豪强、反对兼并。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百业之本”,作为农业生产的载体,土地还象征着财富和权力,土地制度则规定着土地所有权归属以及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
汉朝存在“官田”与“民田”两种性质的土地,前者所有权由官府控制,后者分为农民土地私有与地主土地私有两种类型。
“官田”通常是授予与租赁两种方式并行,其中,授田制给予农民土地耕种权甚至部分所有权,这部分土地变为“民田”,由农民自行生产支配,只需与自耕农缴纳同等赋税。
“民田”方面,名田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原产发还”的原则,秦末战乱前拥有大量土地的仍然是地主,仅有少量土地的则是自耕农。这构成了汉朝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前世”基础。
针对土地兼并问题,汉武帝时期的“调均土地”政策带有“抑强扶弱”意味。“抑强”体现为针对豪强“田宅逾制、以强凌弱”的行为进行督察和打击甚至强制豪强迁徙,禁止商人“名田”,限制其“田宅逾制”。
“扶弱”表现在对农民实行扶助甚至奖励政策。一方面,倡导自耕农“力田”,对“耕垦”行为进行奖励;另一方面,将国有土地以租赁或授予的形式给予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即实行“假民公田”或“赋民公田”。
封建王朝终究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打击豪富”只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无法真正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授田于民甚至奖励农户“力田”以纾缓民生,也只是为了保障赋税徭役来源或者稳固江山。
由于豪强地主对土地的肆意兼并与掠夺,自耕农经济进一步瓦解。西汉末年,庄园制开始萌芽并不断滋长,贫苦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原本处于相对自由租佃关系中的佃农或雇农则向依附农转化,纷纷沦为附庸。
南阳大商人地主樊宏“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就是典型的庄园制经济。东汉后期,庄园制经济体系更为猖盛,“豪人之室,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在“庄园”中从事生产的奴婢和徒附,大多是因土地兼并而失地的流民或是曾经的“佃农”。土地占有两极分化,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名田制”难以为继。
汉初“名田制”授予农民占有小块土地,农民可以通过经营土地获得一定量的生活所需,民生状况逐渐向好。
然而,汉武帝之后土地兼并问题重现并愈演愈烈,豪富依仗经济手段或政治手段侵占农民土地。自耕农破产流亡,沦为佃农、附庸或流民,民生状况迅速恶化。
尽管西汉早期“名田制”赋予了农民一定的土地权利,“休养生息”政策也助力了民生的发展和改善,但这些并非以维护农民利益为目的,只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封建王朝以土地为媒介对民众进行社会控制,内生诸多局限与不足。
汉朝实行定额税,以百亩为征税单位,即使农民实际占有土地不足百亩仍按百亩计税。根据记载,税率为“亩税三升”,但实际征税额往往超出这一数值,农民税负较重。
为维持生计,大量农户被迫沦为豪强地主的“佃户”或“附庸”,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只能依靠租种地主土地或通过其他劳动获得收入。
地主为取得更多土地剩余价值而对佃户进行剥削,经常把赋税负担转嫁于佃户。最终,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收益,而佃户只有尽可能多地投入劳动才勉强支付高额田租和维持生活。
如王莽改制时曾指出“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至东汉,依附农民所受剥削更加严重,“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
依附农普遍生活困苦,经济状况极差且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
此时,“名而无限”的名田制不仅无法发挥其使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充分结合以恢复经济和稳定民生的作用,反而成为恶化土地兼并和民生状况的制度原因。
土地制度规定着土地的权属分配状况以及生产经营方式等,其发展和演化折射了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地关系,反映了期间地权结构和社会关系调整。
与赋税、徭役和户籍等诸多制度密切相关,依循土地制度演变之线索能够剖析当时民生状况;同时,民生实况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晴雨表”,透视土地制度背后的民生演化可知社会发展转型甚至王朝兴替的根本驱动力。
西汉初年,为了稳固统治,推行“名田制”即按户籍以名占田,辅以“休养生息”政策,民生状况有所改善,但由于“名田无限”即放任兼并,官僚地主经常通过买卖或强占等方式不断吞并农民土地,大土地所有制(庄园制)不断扩张,农户纷纷破产变为“佃农”或沦为庄园附庸。
为解决土地兼并导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民生困境,两汉王朝多次颁发“限田令”甚至把“授田制”的对象由军功贵族调整为底层无地农民。
但终归是囿于土地私有制且触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土地兼并问题愈发严重,民生实况持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终致汉王朝覆灭。